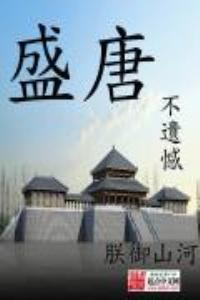白夜浮生錄 第二百二十四回:無人契闊成說
這是哪兒?
白涯摸了摸自己前胸,皮膚和衣服都完好無損,不像是被刀刺穿的樣子。他的刀也很乾淨,沒有一滴血在上面。他看了看地,看了看天,覺得自己無法形容自己所看到的景象。它們是混沌一團的黑,但也不是純粹的黑,感覺有些奇怪的色彩在緩緩變化。就像是一個人閉上一隻眼,睜著另一隻,再用睜著的眼去看閉上的眼的視野。說不出看到了什麼,但至少知道自己還沒瞎。只是廣袤的混沌之中唯獨能看到自己這件事,讓他感到了一種窒息的渺小與孤獨。他舉步維艱。
這裡是天道?不像,完全不。雖然他也沒去過天道,不知道那兒是什麼樣子,但他覺得也不該是這種地方。那麼這裡會是六道的其他地方嗎他不論向前走幾步,都覺得自己是在原地打轉,看不到出路。這算什麼事,還有機會能出去嗎?白涯既困惑又頭疼——尤其對自己還活著這件事。倘若他真的死了,那這裡難道是冥府?
「醒了?」
這是一個近在咫尺的聲音。它的出現並不唐突,像是一種在自己心裡湧現的想法一樣自然。即便如此,白涯還是感到了一定程度的驚訝。當然,不論是誰都會驚訝的。
「長話短說,這裡是六道的裂隙。」
「六道靈脈?」白涯問,「我被困在這裡?」
「是。」那聲音簡單地回答。
不論是這個突兀的、男女不分的聲音,還是白涯自己的聲音,在這個環境中都顯得恰到好處。聲音不會因為空間過小而迴蕩,也不會因為太寬廣而被吞沒。
「你是誰?」
「奈落至底之主。」
「」
白涯感覺這個聲音在和自己開玩笑。
或許是見慣了諸神的大場面,現在與這位自稱傳說中的人物、冥府的老大、奈落至底之主的閻羅魔,與自己的會面竟然是如此的沒有排面。他很難相信此人的這番話,但除此之外,好像也沒有什麼更值得相信的人了。
「那你——您怎麼會在,這種地方?」他狐疑地問,「不應該在冥府麼?」
據說冥府就坐落在人道與地獄道的某處靈脈間。不過都是傳聞,誰也沒見過,見過的恐怕也回不來了。對於這一切,白涯並不感興趣。
「身在冥府,不能來見。聲音,能聽到,這便夠了。」
白涯微微皺眉。他著實無法將這個似男非女的聲音與閻羅魔聯想在一起。這嗓音說不上好聽難聽,但也無法讓他想起任何一個見過的人。分明是從未聽到過的,卻不覺得陌生。當然了,也沒熟悉到哪兒去。就好像這聲音里有一種法術,會讓你固有地出現這種認知,有些刻意。它既不讓人抗拒,也不讓人親切。
它就是一種簡單的事實,簡單地存在著。
「我能聽到。但你是何意?我應該已經死了。而且,我對你的身份並不信任。」
對方沒有回話,也不知是不是生氣了。但在它的眼前,忽然出現了一團怪異的顏色,小小的,像個種子。而後它迅速擴散——以一種白涯無法理解的方式。它像是花在綻放,又像是顏料在染缸里擴散。一些十分衝突的色彩在眼中搖擺、飄動、蔓延,接天連地。最後,他所處的整個環境都成了這樣難以名狀的斑斕,光怪陸離。他覺得有些眼花,試著後退兩步,每一步都令周圍的色塊隨他遷移,使人頭暈目眩。他不得不站在原地,看著那些毫無過渡的冷暖色碰撞、擴張。
接著,那些色彩凝聚出一個輪廓來。一個兔子模樣的色塊在他面前晃動,迎著面跳到他跟前。它動起來也像兔子——但它肯定不是兔子。
兔子開口了。它嘴巴的部分裂開鮮艷的紅色。
「白少俠白少俠!」它的聲音與剛才的聲音一模一樣,但語氣急促得緊,「你一個人在這裡,會不會覺得害怕呀。」
白涯感到莫名其妙。他蹲下身,看著這奇怪的「兔子」。但他還是回答了:
「不怕。我應該已經死了,死人沒什麼可怕的。」
「死人要怕的可多了。」小兔子揮了揮自己的前爪,猩紅的口腔一開一合,「要擔心下一世不知轉生何處,還是不是人間;若在人間,能不能生在一個好人家;若記憶消散,自己又會有多少遺憾;若生前執念太重,做鬼也會感到孤獨。」
第二百二十四回:無人契闊成說
-
秦始皇建立中華第一帝國,漢高祖建立中華第二帝國,李淵李世民父子建立中華第三帝國。而中華第四帝國則由王瀟王毓澤父子,在1895年建立。 炮兵參謀王毓澤重生1890年,成為川西巡閱使府少
-
重生北宋神宗年間的他,在明白了身處的時代背景跟熱血江湖,他就默默許下兩個宏願。一要挽救即將傾覆的北宋朝命運,復興屬於炎黃子孫的漢唐盛世,讓外族不敢輕易踏進國境半步。二要跟前世心目中的悲劇英雄喬
-
和岳鵬舉,唱滿江紅,壯志飢餐胡虜肉,何其快哉!抄辛稼軒,吟破陣子,了卻君王天下事,不亦樂乎?看岳丘穿越南宋,藉助超級兌換系統,譜寫一段熱血的歷史。揚我漢威,岳旗飄揚! 各位書友要是覺
-
雲崢打開了一扇門,就再也沒有回頭路,生活,就是這個樣子,開了弓就沒有回頭箭,想回頭已是百年身。 這是一本講述為師之道的小說,說的是生存智慧,講的是人間溫情,道的是兄弟情義,表的是溫恭謙良,這
-
沒有屈辱和遺憾,只有勝利和輝煌。 鐵軌鋪向哪裡,大唐的利益就延伸到哪裡。 火炮戰車所向無敵,一帶一路再創輝煌。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盛唐不遺憾》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
-
他是僱傭兵世界的王者,他是令各國元首頭疼的兵王!為朋友,他甘願兩肋插刀;為親人,不惜血濺五步!是龍,終要翱翔於九天之上,攜風雲之勢,一路高歌猛進,混的風生水起。 新書《辣手神醫》上傳
-
中華自古就有隱龍守護,皇帝乃真龍轉世,但隱龍的世界恐怕鮮有人知。隱龍者或化身為軍事家保境安民;或化身為改革家,逆轉潮流。 歷史長河中凡是護佑中華並能改變國運之人,都稱之為隱龍。
-
雲從龍,風從虎,功名利祿塵與土 望神州,百姓苦,千里沃土皆荒蕪 看天下,盡胡虜,天道殘缺匹夫補 好男兒,別父母,只為蒼生不為主 手持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安忍不動如大地,靜慮深密如秘藏!地藏捲軸突現世間,黃金鳳凰再臨天地,南北爭雄,密雲重重。深宮詭虞,疆場喋血。以天地為棋盤,眾生為弈子,英雄豪傑,風月美人,演一出曠世棋局!本書官方群:7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