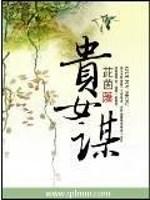梟起青壤 11 ⑩
天已經全黑了。
車內開了前側的閱讀燈,昏暗的冷光調,微微泛熒藍,高處路道連過路車都少有,細長身條的野麻叢叢縱縱,把車子裹在中央,帶出深重的隔世感。
炎拓拈著那個手壓式注射針筒,翻來覆去,看了有一會了:那個叫板牙的村子讓他捉摸不透,真是自己倒霉、碰巧進了一個賊村嗎?可要說是衝著他來的
真是荒唐,他從來沒去過那個村子,連這個市,都是生平頭一遭來。
聶九羅坐在一邊,不聲也不動,只偶爾伸手、拈撥左腕上的螺紋手環,環身相擦相碰,發出極細碎的輕響。
這聲響引起了炎拓的注意,他看了一眼聶九羅:「你是幹什麼的?」
***
炎拓的運氣還算不錯,那老頭雖然將注射針筒插進了他的後頸,卻沒來得及推入太多針劑,他得以爭取到片刻的清醒:最要緊的是妥善隱藏自己和這輛車,被這村子的人追上、暈在半路或是被警察發現,後果都不堪設想。
所以車子上路之後,他儘量選擇沒有攝像頭的偏僻路道,然後相中了這片野麻地——野麻是高杆作物,桿身足以沒過並遮蔽車子——開進野麻地之後,他還特意拐轉了幾個彎,停在最深處。
一般的司機都要趕路,來去匆匆,八成都不會注意到這裡「撞過車」,即便注意到了,也少有那個閒情過來查看,而過來查看的,要麼是真熱心,要麼是包藏禍心。
起初,他以為自己是遇上熱心人了,留下聶九羅,是因為她看到了不該看到的,但再一想,這路人出現的次數,有點太多了。
尤其是在他被攻擊之後,第一個找過來的,居然是她,而且,她的臨危表現也出人意料——老錢固然是被她用藉口支走的,但如果不是她表現得那麼自然,老錢也不會走得那麼痛快。
知人知面不知心,誰知道她是不是那個板牙村放出來追咬他的狗呢?
聶九羅說:「我手機上有微博,實名認證,也有微信,都在上頭了。」
她覺得這個炎拓,並不窮凶極惡:真正兇殘的人,早一槍一個,把人撂倒在野麻地里了。他肯讓老錢走,其實釋放出一個相對溫和的信號。
炎拓拿出手機,用她的臉解了鎖,先點進微博看。
看不出來,她是做雕塑的,還小有名氣,博上有幾十萬的粉,這微博是工作相關,展示的都是作品,炎拓即便是外行,也看得出她的作品很有個人風格,細膩處帶妖冶,溫情處滲涼薄,劍走偏鋒得恰到好處。
他一張張點進了看,不時放大:「都是你塑的?」
聶九羅嗯了一聲。
炎拓沉吟了一下,驀地去拿聶九羅的手。
聶九羅一怔,下意識縮手,不過慢了一步,炎拓的指腹從她掌心一路摩挲、拖過指腹,力道很輕,若有若無的觸碰,卻激得她小臂微微發麻。
「你手不粗啊,做泥塑是手工活,手指一般都粗糙。」
聶九羅微蜷了手、籠住掌心:「注意保養、肯花錢,手粗不到哪去。」
這倒也是,手是女人的第二張臉,現在的年輕姑娘,但凡經濟允許,在保養上都不會吝嗇。
炎拓繼續翻看微博,雕塑是個功夫活,她的作品並不多,只翻了十多頁,就已經翻到了兩年前。
有認證,有作品,基本做不了假。
他說了句:「塑得還挺好看。」
然後退出來,又點進微信,聶九羅微擰了下眉,覺得隱私被觸犯到,再一轉念,反正也沒什麼隱私。
聶九羅的微信好友不少,工作夥伴為主,也有家政、快遞、護膚美甲,炎拓大略看了看,知道了不少事,比如她有個住家阿姨叫盧姐,上一條消息是上周的,問她白米蝦是鹽水煮還是爆炒;比如她院子裡種了不少花和樹,花匠兩周去一次,處理普通人應付不了的蟲害葉病;再比如她有尊作品,三年了都沒完成,對接的那個老蔡發牢騷說「三年了,你好意思再拖嗎?這生孩子生快點,三年都三四個了」。
炎拓覺得這個老史說話還挺嚴謹,三年三四個,充分考慮到了生雙胞胎的可能性。
他正要說話,機身微微一震,有新的消息進來。
不是簡訊,也不是微信消
11 ⑩
-
黑玫之家是一群美艷少婦們合租的別墅公寓,她們成熟性感,她們惹火撩人。陶寶陰差陽錯的住了進來,然後,他驚訝發現......
-
宅斗是可怕的蘇九一向知道,真正穿越了這才知道宅斗要素中的豬隊友狼對手都可以弱爆了,可怕的是披着羊皮的狼隊友,叼着血淋淋的肥肉硬要她吃下,再肥美的肉也是人肉啊!這怎麼破?
-
系統流看多了,系統做主角不多吧?作者君沒搜到,所以有了這本書。 「確認綁定,系統插入中……插入1%……插入1.5%……」 「姑娘,能不能配合一點,再反抗信不信分分鐘抹殺你……什麼是系統?我
-
「一年後,我們離婚,互不干擾。」 季憶之所以答應賀季晨假結婚,是因為她堅信完美情人賀季晨絕對不會愛上她。 婚後假戲真做不說,一年後,別說是離婚,就連離床都..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腹黑慵懶巨有錢男主vs高嶺之花藏得深女主】秦苒,從小在鄉下長大,高三失蹤一年,休學一年。一年後,她被親生母親接到雲城一中借讀。母親說:你後爸是名門之後,你大哥自小就是天才,你妹妹是一中尖子生
-
無意間觸電後的張易,發現自已竟然可以隱去身體,變成一個透明人,意外的驚喜讓他開啟了新的人生。 一個會隱身而行走在都市中的奇人。 你看不見我,你看不見我,你看不見我…… 保鏢新群:2417
-
啞女郭清雅穿到異時空的水鄉農家。這是一個完美而又絕妙的家庭組合。因此,前世安靜了二十四年的啞女,今世人生處處峰迴路轉、時時撥雲見月,她的故事,從一場橫刀奪愛開始……(新書《日月同輝》已上傳,懇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未到四十她便百病纏身,死的時候兒子正在娶親。錦朝覺得這一生再無眷戀,誰知醒來正當年少,風華正茂。當年我痴心不改;如今我冷硬如刀。——————————本書已簡體出版,當當網、京東、亞馬遜均可訂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