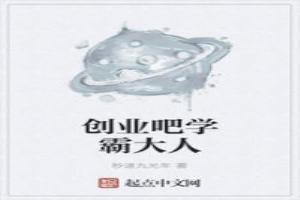陰陽石 堯裊無期——緣落筆中還好有你
堯裊無期緣落筆中還好有你
風攪動了墨池,澆在薄雲上,成了頭灰色的水牛,人們叫它雨神,它如此敷衍而吝嗇,施捨般僅僅拋灑出了一粒雨滴。
一粒雨,如何才能冷滅世間所有惱火的面色,所以時間也為它憐惜,在那雨滴匆匆落下的生命里,給了它選擇時刻的權利。它落下了,落到了這個無情世界之前的,那段光陰。
滴答....
雨落在了一片荷葉上,擎拿著荷葉的女娃,將那滴雨傾落到地上,卻剛好點到自己的鞋尖,而這滴雨,似乎是剛剛那場濛濛細雨中的,最後一滴。
她沿著田道走回家,腳上那雙繫繩的藍布鞋總會往泥濘的土裡壓進幾寸,而她的家,是十多座木閣樓,方圓十里內,也只有她這一家人住著。
她叫白裊兒。
裊兒走到家門口時,看到了那輛載滿人的馬車,馬車頂檐上掛了兩串玉板,顛簸之時,它們總能敲打出怡人的曲子,來為漫長的旅途添一點趣味。
馬車的主人是婁家人,婁家老邁的爺兒不遠千里趕來,例行每年對故友的祭拜,今年怕是最後一年了,他走不動了,兩家子孫之間已經無多少情感,待他逝去,怕是再無聯繫了,所以,他此次帶來了一個孩童,也帶來了一紙婚書。
他叫婁君堯。
兩家人匆匆相處了一日,便要分別,白裊兒甚至並沒有見到自己的「未婚夫」,兩家家主互換了一塊玉佩,指為將來認親信物,也許是這個時間的人們,感情並不徹骨,所以少了許多寒暄,沒了許多留戀,只在那一陣陣玉板碰撞的脆聲中,了了的揮了揮手。
從那天起,白裊兒要開始寫信,即使她識字不多,即使她還不懂得什麼叫婚姻,即使她對未婚夫的了解只是一個姓名。
那時的天空,也是有明月,也是有烈陽,人們過得依舊是日子,它一刻刻的拔起了禾苗,催黃了果子,讓女娃鼓起了胸脯,讓男娃長起了鬍鬚。
白家的人,一天天的少了,一半的樓被掛上了鎖,木窗都要關嚴實,也不需人去打掃。十里方圓一戶人,能留下來的只有那些年邁的家僕,年輕人走了,白家的兒子夭折了兩個,走了兩個,而那個時候,姓氏並不是難以改變的鴻溝,為了生存,誰都可以姓白,誰也可以不再姓白。
白裊兒每天都要寫一封信,再託付給趕馬車的老家僕送到十里之外的村莊寄出,兩三年後,老家僕埋入了土,她便自己踩著雙繫繩的藍布鞋,一步步走去,然而她卻從未收到過一封信,這是那個時候人們的規矩,寫信是女子的「任務」,她得到的是每年男子寄來的禮物。
婁家是在人族中區,那個時候生靈之間沒有分界,人族左側便是獸族,右側便是異人族,戰爭總是朝起晚落,每一天都會有人死去。
婁君堯十歲就被選進了軍隊,那時起隨身要準備兩把匕,一把殺敵,一把自盡,在與死神博弈的時間裡,讓他的心還保持著希冀的,正是裊兒的一封封信,他時常要挑一些東西寄出去,一個盔甲,亦或是一件花袍,他不懂得姑娘家喜歡什麼,直到有一天,裊兒在寄給他的信封里,偷偷藏了一條手帕,那是她親手繡的。
君堯有些生氣,因為女子給男子寄禮物,是對男子家室的羞辱,但他還是留下了那條手帕,只是一年裡不再寄給裊兒禮物,以傳達自己的不滿,那個時候,裊兒的家裡已經就剩下三個人了,她,她的父親,還有一個老僕。
戰爭總會為時間劃上些明顯的轉折符,人族敗了,敗給了異人族,異人與人極像,卻天生有獸的力量,白家隱居田野的作為起效了,在十里外的村莊被屠戮之時,裊兒還安詳的吃著白粥,誰也沒有現這裡還有一戶人家。
婁家亡了,被闖進的異人血洗,君堯隨著軍隊西逃,躲過了一劫。異人實行安民的政策,他們殺戮之後露出善臉,給人類生存的權利,城還是城,人還是人,只是主子變了。人類從此與異人族合二為一,異人冒著被染污血統的危險,與人類交好,也只是為了能在這萬萬種族之間,多一份活下去的保障,而兩方合併後,獸人族果然忌憚了很多,時間又恢復了安定。
婁君堯逃出了軍隊,跑回了自己的家鄉,家園已是殘垣斷壁,人也成了一堆堆白骨,即便在軍隊裡待了那麼久,他依舊無法接受,他殺過異人,拋頭露面或許會被認出,他惶惶度日,終究是瘋了
-
郝仁,人如其名,是個好人,理想是平平安安過一輩子,當個窮不死但也發不了財的小房東——起碼在他家裡住進去一堆神經病生物之前是這樣。 一棟偏僻陳舊的大屋,一堆不怎么正常的人外生物,還有一份來自「
-
魔王! 恐怖與邪惡的象徵!殺戮與死亡的代名詞!可真魔國卻迎來了一個史上最不像魔王的魔王! 「魔王陛下,這份文件請您簽署,但請注意不要把手放在不該放的地方。」 「亞林大人,人類軍隊來襲,不
-
羅佳,姓羅的羅,上好佳的佳。 地球科技界最大幕後黑手,沒有之一。
-
這是一個充滿了星力的平行世界。星圖、星技、星寵、覺醒者大行其道。魂穿而來的江曉,體內蘊含着一張奇特的內視星圖,成為一名稀有的醫療系覺醒者。他本想成為一隻快樂的大奶,但卻被眾人冠上了毒奶之名。這
-
白小飛搶紅包得搶到了一個時空穿梭器,擁有了穿越無盡時空的能力,然後在成神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和諧的世界,變得無比瘋狂! 風暴席捲而來! (新書是幼苗,需要大家的呵護,求收藏求票票,感激
-
本書屬於慢節奏半同人作品,雙線,主世界+副本世界 完結篇: 冰與火之歌、邪惡力量+美恐3,天賦異稟、大群、X戰警、加勒比海盜、地獄神探(電影)、精靈寶鑽。 ……
-
科技圖書館:科學的至高境,就是神學; 長生不老,飛天遁地,呼風喚雨,移山填海。這些神話傳說,科學是可以實現的。想拿這些技術,必須擁有科技圖書館最高權限。 一次意外的救人,讓陳默收穫了愛情,
-
那一天,一道天雷劈下,王旭沒有穿越,他家的大門穿越了。 電影,電視劇,動漫,小說,遠古神話,這裡有無盡的時空,也意味着無盡的可能.... 普通群:260616572《無加入要求》 vip
-
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宅男90年後劉瑞安,莫名其妙來到了漫威世界之中。 從此,為了能夠生存下去、為了能夠尋找到回家的路,不得不靠着能夠穿越其它世界的金手指努力變強起來。
-
艾莉亞-史塔克想要殺死自己死亡名單上的所有人,哆啦A夢想讓大雄的成績好一點,蜘蛛女俠格溫想救回自己死去的男朋友彼得-帕克...... 化身神龍,行走諸天萬界,滿足他們的願望。 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