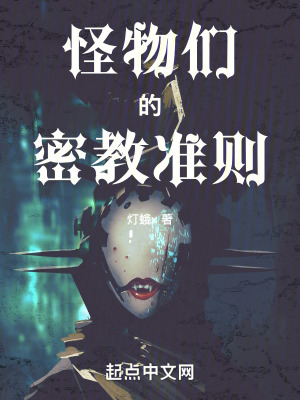白夜浮生錄 第五十四回:來者可追
吟鵷正胡思亂想,絲毫沒有察覺到什麼東西紮上自己的手指。但一滴殷紅的血就是滲了出來,她還有些驚訝。緊接著,她就有些不適了。並非是疼痛,而因為她不喜歡紅色。
看不見的針引出血,落到飄過來的符咒上,像有個透明的手遞過來一樣。這細不可見的傷口很快就癒合了,連送到自己嘴邊用唾沫舔舔的工夫都不用。血在寫了奇怪符文的紙上略微擴散,隨著一陣風飄回凜天師的手中。他說道:
「在作法前,我得先告訴姑娘有了這指尖血,我或許會得知一些姑娘的私事。至於能看到什麼,都要隨您自己的心性。每個人都有秘密,有人怕別人知道,就能保護得十分緊密;但有人越怕被人知道,秘密越容易顯露出來。我不會去抓那些雜念,只會打撈有用的東西,除非這二者有重合的部分。也就是說,我無意窺探您的隱私,卻依然存在這種可能。我得先把話給您說明白。」
吟鵷知道天師只是告訴自己,而沒有詢問的意思。但這時候她並不覺得被冒犯。自己再怎麼身世顯赫好吧,也不是特別顯赫,總的來說也是平民一個。能驚動六道無常與這種避世高人,恐怕自己的麻煩絕不會小,她完全理解每一方的處境。何況她認為自己並沒有什麼值得隱瞞的事。
哪怕是那些事,聽上去血淋淋的、殘酷的事。
她從來無意隱瞞,反正其實全天下都知道了——只是若誰要提起,便像撕開她的血痂一樣痛苦。若是大家誰都心知肚明,只是心照不宣不去提及,倒還好受些。儘管這聽上去像逃避責任,可還有什麼是她所能承受,什麼又是她所不能承受的?
一句老話:來都來了,就算她不樂意,還能從山上跳下去不成?沒必要,事情也沒嚴重到那個份上。她點了一下頭,就一下,但幅度很大,是下了決心。
「如此,凜某便放心些,即便我知道,這還是有些對不起姑娘,多有得罪。陣法我早已歸置完畢,兩位且隨我來。現在正是適合作法的時機,耽誤不得。一會我坐在陣法的東邊,吟鵷姑娘坐在西邊,我們的距離不超過一尺。水無君站在陣法三尺開外便可,切莫離太近。不然陣法周轉起來,可能會受到影響。」
水無君點點頭,牽著吟鵷隨他走過去。凜天師一揚手腕兒,符咒飄出去,懸停在一處空地上。空地忽然以它為圓心,擴散出一個發著微光的圈來。說不定這光芒很強烈,只是大白天的看不出來罷了。凜天師踏入陣內,腳下沒有一點聲音,但吟鵷似乎聽到有節奏的一個鼓點。按照天師的意思,她也走進去,又聽到了那聲響,之後便不再有了。
兩人面對面,如打坐般閉眼盤腿,中間就是那道沾血的符咒。天師說了,不論發生什麼都不要睜眼,除非聽到他的允許。水無君知道,他是要「入定」,以窺探吟鵷的因果。這法子若不是有著高強的靈基,恐怕是要折壽的。對凜天師而言亦是如此嗎?水無君不太清楚,因為他好像這樣幫過很多人。在她的概念中,幾百歲的仙人並不少見,他這樣就說自己已經老了,是不是與此有關?仙人們或廣結仙緣,廣收弟子,以求仙緣;或閉關自守,不問世事;或煉丹煉藥,清身凝神。獨獨這凜天師雲遊四海,行善積德。這麼做的人不是沒有,但都是順手的事,沒誰把這當正經活干。歸根到底,仙人修行多是為了卻塵緣,得道飛升。這人好像不在乎自己離天界有多近多遠,就這幾年才老老實實找了一處山頭,琢磨著再活久點,多幫些人。反倒他人還沒死,多少廟宇都供上了香火,也算奇景。
剛想沒多久,那法陣中央的符咒忽然燒完了,一撮灰燼就從她眼前迎面而來,嚇了她一小跳。她錯臉避開,那灰燼羽毛似的竄到天上。就在這一刻,風起雲湧,一瞬間滾滾白雲都像是加快了前進的步伐。這也是錯覺嗎?或許只是普通的光影游移罷了。但能讓太陽的光芒也變幻莫測,這究竟是什麼法術?
水無君看著他倆,也不敢說話。凜天師始終是那樣平靜,雕像似的一動不動,反觀葉吟鵷,不知為何緊鎖著眉,略收下顎,一副受刑似的模樣。她有點擔心,又因對凜天師充分信任,才沒有做出任何詢問。
凜天師看著是挺安靜的,自己所見卻又是另一番光景。他像一支箭,一陣風,一隻鷹,在無數場布局不一又沒有銜接的戲台上穿行。巨大的信息流湧入眼裡,灌進心中,他敏銳地去捕捉那些有用的部分。
-
昔日頂級工程師衛三穿成星際失學兒童,靠着撿垃圾變廢為寶,終於趕在開學季攢了一筆錢,立刻要去報名上學。 她打算將來成為一個機甲師,據說特別賺錢,還和自己本行息息相關,計劃通√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本想養只小奶狗,結果是條瘋狗。皇子x太監 原創小說 – 古代 – BL – 中篇 皇子x太監 (真貌美太監) 受重生 年下 前期都是戲精,一個裝乖一個扮溫柔 雙惡人,攻有點瘋 ..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簡介: 林昊穿越到萬族林立的玄幻世界,入贅趙府的姑爺。原以為就要這樣憋屈的度過餘生,卻綁定了神級進化動物系統。 「叮,您的蒼蠅殺手已強化雙爪,攜帶金屬武器,鋒利如刃!」
-
唐門外門弟子唐三,因偷學內門絕學為唐門所不容,跳崖明志時卻發現沒有死,反而以另外一個身份來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屬於武魂的世界,名叫斗羅大陸。這裡沒有魔法,沒有鬥氣,沒有武術,卻有神奇的武魂。這
-
簡介: 你是否想過,在霓虹璀璨的都市之下,潛藏着來自古老神話的怪物?你是否想過,在那高懸於世人頭頂的月亮之上,佇立着守望人間的神明? 你是否想過,在人潮洶湧的現代城市之中,存在
-
暫時無小說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