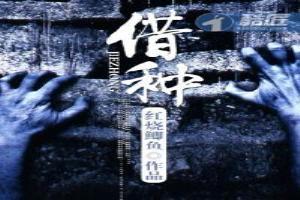玄門妖修 六六七 可笑南疆螳螂斧,何御鈞天隆車隧(一)
更新:08-18 22:06 作者:離經叛道 分類:仙俠小說
又有長老開壇講道了
每當這個時候
這般積極
靠近妖王峰的雲霞之上
他身邊有個膚色白皙
這兩個弟子為數萬弟子中中上之輩
倘若在凡俗之中
王伯藝懶洋洋地看了李猖幾眼
也不見他入得動作
一股清爽的草木馨香頓時彌散開來
李猖卻眉頭微皺
王伯藝微微一笑
這弟子口中的許師叔
許聽潮知曉自家缺陷
這般偷懶的法子
許聽潮終究是有其長處的
雖然不曾聽過幾回
王伯藝只是一笑
王伯藝認為自己雖然表象懶散了些
執著酒杯
心念及此
-
簡介: 天下已紛亂三百餘年。 中原歌舞不絕,異族厲兵秣馬,江湖劍仙縱橫,名將鎮壓十方。 距離天下大亂還有五年,年少的藥師李觀一雨夜殺人。 終於睜開眼睛,看到這人間亂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header
-
天玄大陸! 威震天下的逍遙魂皇葉逍遙,意外在玄域隕落! 百年後,他重生於流雲國星玄學院被人欺辱的學員葉玄身上,從被人嘲諷的廢武魂、死脈,到傳說中的逆天三生武魂,他從此踏上一段震驚大陸之旅!
-
有一天,我在公交車上忍不住摸了有錢人的二奶,我忐忑不安。結果美女非但沒生氣,反而跑來求我「借種」 ……
-
漢末亂世,群雄並起,只為爭奪那九五至尊之位。 這裡不僅有終極天命在身的秦日天,更有位面之子劉秀,秦皇...
-
簡介: 你是否想過,在霓虹璀璨的都市之下,潛藏着來自古老神話的怪物?你是否想過,在那高懸於世人頭頂的月亮之上,佇立着守望人間的神明? 你是否想過,在人潮洶湧的現代城市之中,存在
-
奇怪性癖的妹妹竟然對我圖謀不軌…… 」哥,你是我的NTR,誰也不能搶走我那還沒捂熱的玩具。」妹妹那空洞的眸子望着我說道。 」我的妹妹竟然把我當成了玩具!!!」我抱着頭髮出悲鳴聲
-
又名:吸奶伯爵 起點女頻強人說:當書名過於YD時,用水果代替!! -------------------------- 中國黑道太子兼血族繼承人楊威因
-
簡介: 作物種植,畜牧培育,礦物煉金......穿越到這個糟心的中世紀大陸,羅德翻開一同而來的巫師指導手冊,橫豎睡不着。 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隙里看出滿本寫着的種田兩字。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