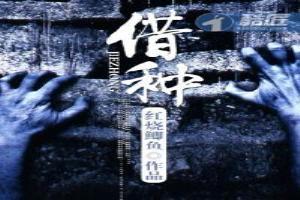東周列國志 第六十六回殺寧喜子鱄出奔戮崔杼慶封獨相
話說殖綽帥選卒千人,去襲晉戍。//www。\\三百人不勾1一掃,遂屯兵於茅氏,遣人如衛報捷。林父聞衛兵已入東鄙,遣孫蒯同雍鉏引兵救之。探知晉戍俱已殺盡,又知殖綽是齊國有名的勇將,不敢上前拒敵。全軍而返,回復林父。林父大怒曰:「惡鬼尚能為厲2,況人乎?一個殖綽不能與他對陣,倘衛兵大至,何以御之?汝可再往,如若無功,休見我面!」孫蒯悶悶而出,與雍鉏商議。雍鉏曰:「殖綽勇敵萬夫,必難取勝,除非用誘敵之計方可。」孫蒯曰:「茅氏之西,有地名圉村,四圍樹木茂盛,中間一村人家。村中有小小土山,我使人於山下掘成陷坑,以草覆之。汝先引百人與戰,誘至村口。我屯兵於山上,極口詈罵。彼怒,必上山來擒我。中吾計矣。」雍鉏如其言,帥一百人馳往茅氏,如探敵之狀,一遇殖綽之兵,佯為畏懼,回頭便走。殖綽恃勇,欺雍鉏兵少,不傳令開營,單帶隨身軍甲數十人,乘輕車追之。
雍鉏彎彎曲曲,引至圉村,卻不進村,徑打斜往樹林中去了。殖綽也疑心林中有伏,便教停車。只見土山之上,又屯著一簇步卒,約有二百人數,簇擁著一員將。那員將小小身材,金鍪繡甲,叫著殖綽的姓名,罵道:「你是齊邦退下來的歪貨!欒家用不著的棄物!今捱身在我衛國吃飯,不知羞恥,還敢出頭!豈不曉得我孫氏是八代世臣,敢來觸犯!全然不識高低,禽獸不如!」殖綽聞之大怒。衛兵中有人認得的,指道:「這便是孫相國的長子,叫做孫蒯。」殖綽曰:「擒得孫蒯,便是半個孫林父了。」那土山平穩,頗不甚高。殖綽喝教「驅車!」車馳馬驟,剛剛到山坡之下,那車勢去得兇猛,踏著陷坑,馬就牽車下去,把殖綽掀下坑中。孫蒯恐他勇力難制,預備弓弩,一等陷下,攢箭射之。可憐好一員猛將,今日死於庸人之手!正是:「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多在陣前亡。」
有詩為證:
神勇將軍孰敢當?無名孫蒯已奔忙。
只因一激成奇績,始信男兒當自強。
孫蒯用撓鉤搭起殖綽之屍,割了首級,殺散衛軍,回報孫林父。林父曰:「晉若責我不救戍卒,我有罪矣。不如隱其勝而以敗告。」乃使雍鉏如晉告敗。
晉平公聞衛殺其戍卒,大怒,命正卿趙武,合諸大夫於澶淵,將加兵於衛。衛獻公同寧喜如晉,面訴孫林父之罪,平公執而囚之。齊大夫晏嬰,言於齊景公曰:「晉侯為孫林父而執衛侯,國之強臣,皆將得志矣。君盍如晉請之,寓萊1之德,不可棄也。」景公曰:「善。」乃遣使約會鄭簡公一同至晉,為衛求解。晉平公雖感其來意,然有林父先入之言,尚未肯統口1。晏平仲私謂羊舌肹曰:「晉為諸侯之長,恤患補闕,扶弱抑強,乃盟主之職也。林父始逐其君,既不能討,今又為臣而執君,為君者不亦難乎?昔文公誤聽元+i之言,執衛成公歸於京師,周天子惡其不順,文公愧而釋之。夫歸於京師,而猶不可,況以諸侯囚諸侯乎?諸君子不滿,是黨臣而抑君,其名不可居也。嬰懼晉之失伯,敢為子私言之。」肹乃言於趙武,固請於平公,乃釋衛侯歸國。尚未肯釋寧喜。右宰谷勸獻公飾2女樂十二人,進於晉以贖喜。晉侯悅,並釋喜。喜歸,愈有德色,每事專決,全不稟命。諸大夫議事者,竟在寧氏私第請命,獻公拱手安坐而已。
時宋左師向戍,與晉趙武相善,亦與楚令尹屈建相善。向戍聘於楚,言及昔日華元欲為晉、楚合成之事。屈建曰:「此事甚善,只為諸侯各自分黨,所以和議迄於無成。若使晉、楚屬國互相朝聘,歡好如同一家,干戈可永息矣。」向戍以為然。
乃倡議晉、楚二君相會於宋,面定弭兵交見之約。楚自共王至今,屢為吳國侵擾,邊境不寧,故屈建欲好晉以專事於吳。
而趙武亦因楚兵屢次伐鄭,指望和議一成,可享數年安息之福。兩邊皆欣然樂從,遂遣使往各屬國訂期。
晉使至於衛國,寧喜不通知獻公,徑自委石惡赴會。獻公聞之大怒,訴於公孫免余。免余曰:「臣請以禮責之。」免余即往見寧喜,言:「會盟大事,豈可使君不與聞?」寧喜艴然曰:「子鮮有約言矣,吾豈猶1臣也乎哉?」免余回報獻公曰:「喜無禮甚矣!何不殺之!」獻公曰:「若非字氏,安有今日?約言實出自寡人,不可悔也。」免余曰:「臣受主公特達2之知,無以為報,請自以家屬攻寧氏,事成則利歸於君,不成則害獨臣當之。
第六十六回殺寧喜子鱄出奔戮崔杼慶封獨相
-
有一天,我在公交車上忍不住摸了有錢人的二奶,我忐忑不安。結果美女非但沒生氣,反而跑來求我「借種」 ……
-
詭秘世界第二部。 1368之年,七月之末,深紅將從天而降。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鑄劍大師凌天鑄劍五萬把,功成一刻魂穿異世,附身卑賤劍奴之身,凝成萬劍之體,身懷絕世火種,覺醒最強武魂,強勢崛起,一路逆襲,坐擁眾美,傲視九天! 會煉器,能煉丹,懂音律,會做菜。麻麻說
-
弱者聲嘶力竭,亦無人在乎,強者輕聲細語,卻能深入人心。一棵熊熊燃燒的天賦樹,每一片葉子都承載着不同的靈紋,宗門被滅,淪為礦奴的陸葉憑此成為修士,攪動九州風雲。...《人道大聖》
-
簡介: 這是一個大洗牌的時代,舊霸主已經退位,新霸主尚未上位!這是一個回到過去,在這個大洗牌的時代,最終成為當世第一財閥的故事。 國家擁有財閥?分明是財閥擁有國家好吧!本書又名
-
蒸汽與機械的浪潮中,誰能觸及非凡?歷史和黑暗的迷霧裡,又是誰在耳語?我從詭秘中醒來,睜眼看見這個世界: 槍械,大炮,巨艦,飛空艇,差分機;魔藥,占卜,詛咒,倒吊人,封印物……光明依舊照耀,神
-
好消息:穿越了,帶系統,登頂武林通緝榜,成為了盡人皆知的魔頭。壞消息:滅門案,養鬼案,屠村案,萬人血坑,荒野屍佛.....狗系統都栽贓給我了,我當了背鍋俠,成兇手了,並且也變強了。懸賞金額一百
-
暫時無小說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