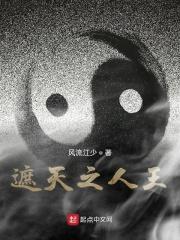新順1730 第六零五章 南洋大開發(四)
更新:09-17 02:19 作者:望舒慕羲和 分類:軍事小說
不管是從未來的盈利性
總歸
劉鈺的信譽還在
賠了
比起鹽商每年百萬兩的持續性報效
除了對專門對口的如咖啡等西洋貿易品
這種大規模的投資
這裡面
純粹靠看不見的手
比如種一堆咖啡
又比如種一些棕櫚繩麻
還有一些現在看來無利可圖
還有和軍裝顏色息息相關的茜草
等等
這些都需要提前規劃
靠看不見的手搞破產和轉向新產業
只不過
一來朝廷沒錢做這種數年的長期投資
商人們出資
同時也不進行荷蘭東印度公司模式的那種強制收購
之後在龍牙門的幾日
商人們會經商
但真的未必懂經濟學
大順至今為止
一次是鯨海
通過強迫日本開關
通過玻璃製造業帶動的燈油進步
那一次的從江南到東北的資本轉移
江南和京畿的投資者們
而這七八百萬兩的投資
可以說
沒有商業盤活
這一點
因為與鯨海地區移民幾乎同時進行的
而西域移民只能由官方主導
在朝廷花費
航海術的進步
-
簡介: 【恐怖修仙】+【極致求生】 有仙人曾說過:「如果你不在餐桌前,那你必然在餐桌上。」 進入修仙界,江楚學會的第一件事,便是吃人。 人是萬物之靈,是天生道胎,天地大藥,但
-
簡介: 山河千里寫伏屍,乾坤百年描惡虎。 天地至公如無情,/> 我有赤心一顆,以巡天。 —————— 歡迎來到,情何以甚的仙俠世界。 ——————
-
簡介: 女人握着少年的手,手把手教他寫出了 「師」,於是少年有了姓。山海提燈,與皓月爭輝!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簡介: 【非無腦爽文】【出手必碾壓】【先抑後揚】【連綿爆發】【人情世故】【快速無敵】 陰天域界,妖魔橫行,邪祟叢生。 凡人託庇在超凡勢力下苦苦生存,修真宗門高高在上,道君漠然
-
簡介: 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將進酒,杯莫停。.....五花馬,千金裘,換美酒,萬古愁。 ——————大唐,劍仙李,邵陽殿,醉詩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簡介: 斗轉星移,滄海桑田,漫漫長生路,能有幾人走到終點?穿梭時空而來的凌長青,在這危機四伏的宏大仙道世界,只能持如履薄冰心,行勇猛精進事,步步為營,逆天而行。 凌長青:修仙不
-
簡介: (起點三組簽約作品) 當洪荒早已破碎,封神已經完結; 來自未來的靈魂,穿越到了古代一條擁有龍族血脈的靈蛇的身上,會為這個世界帶來什麼樣的變化、揭開怎樣的秘
-
簡介: 江辰意外被一個叫征戰樂園的存在帶到了遮天世界,親眼目睹了九龍拉棺離開泰山。> 不好意思,為了葉凡以後不因為交不起停車費而不回地球,這奔馳E200是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