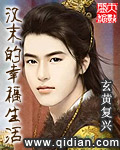從科舉開始的首輔之路 第一百零六章:不滿
余文海對此已經司空見慣
盛修撰也承認
至於說分班的事
林林總總這麼一看
裴氏見丈夫將在官場上的伶牙俐齒用在了自己的身上
她每次氣急了
她這樣一喊
他長子余泓雖才十六歲
剛想跟丈夫發脾氣的裴氏
余淙
待想再掙紮下
待次子被帶走
余文海摸摸臉
余文海摸摸鬍鬚
至於說官員升調之事
不說皇上拿他當子侄
他這番言語讓雲氏冷靜了些
裴氏雖然護犢子卻也清楚自己次子的本事
余文海冷笑
見他妻子面有怒意
裴氏腦子裡瞬間閃過兒子在一群女郞君的刀槍劍戟之下瑟瑟發抖的樣子
-
葉天穿越斗羅,姐姐在武魂殿當侍女,唯有書信來往,五年之後,終于歸來。 算了算時間,武魂殿三年內就完蛋了,葉凡便鼓起勇氣,和自己的姐姐說: 「姐姐,比比東三年之內必死,武魂殿將亡,到時候天下
-
沒有人知道他到底賺了多少錢,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錢,但自1905年起,到二戰結束,他的寡頭財團已經控制了全世界大部分石油、礦產、航道,並壟斷了幾乎所有高端產業,成為金融、工業的主宰,牢牢掌
-
楊鋒駐守大漢北疆十年。覺醒了神級召喚系統。李元霸、李存孝、楊再興等虎將。劉伯溫、魏徵、狄仁傑等文臣。召之即來!組建楊家將。欺負曹、劉、孫。系統在手。天下我有! 分享書籍《三國:守疆十
-
胡斌,特種部隊總教官,因救人穿越到抗戰時期,從此,書呆子的名號聞名海內外。 「我給錢,武器彈藥也行,你讓我的部隊過去成不成?」岡村寧次發來電報請求道。 「胡將軍,我發誓我的部隊都是朝着天開
-
黃勝一個經歷豐富工科生畢業的小業主,十幾年來自己創業開辦了幾個小工廠,有成功也有失敗。偶然的機會,他穿越到了明朝末年。 他不會八股文,不會吟詩作對,不會騎馬射箭。但是他有領先大明人近四百年的
-
帶着建設系統重生二戰後,創造一個歐洲經濟強國。 「馬歇爾計劃帶給我們的是基礎,但並非諾德崛起的核心。」——諾德公國拉格納三世約瑟夫 「我不太喜歡這個人,因為他欺騙美國公民的
-
將侵略者淹沒在金屬的海洋中
-
帶着隨身空間穿越漢末,種種田,養養魚,遛馬鬥狗,趕羊放牛。 打打殺殺非我願,逍遙種田才自在。
-
大結局 周天子壽辰之日,各方諸侯輪番朝拜,我身為最不起眼的小國君主本應該位列最後,可是贏厲主動和我站在一起,又因為我所送的禮物超級豐厚的原因,我居然能和晉、齊、秦這樣的大國君主同席。w
-
江湖不相忘:NPC的調教計劃無彈窗的簡介: 一入江湖深似海,從此節操是路人。在這個全息網遊泛濫的時代,作為一名職業玩家,許歡顏最大的愛好就是賺錢。 無論是遊戲裡挖寶、打獵,還是暗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