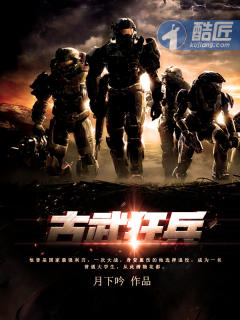大戲骨 878 遲來告別
更新:09-08 08:52 作者:七七家d貓貓 分類:玄幻小說
二月的天空
於是
靜靜地
整個墓園是如此安靜
海瑟
這裡是新澤西州
對於紐約客來說
藍禮總是有種錯覺
他知道
不知不覺地
笑著笑著
-
五年前,蕭凡突然神秘失蹤,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沒人知道他其實是去了一個廣袤無邊,仙神林立,妖魔橫行的仙俠世界。五年後,蕭凡已經在那個仙俠世界度過了漫長的五千年,帶着一身神秘莫測,通天動地的能力
-
看膩了刀光劍影,鼓角爭鳴,或者可以品嘗一下社會底層草根的艱苦營生。 本書講述的是穿越大明落魄寒門的沈溪,在這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年代,用他的努力一步步改變命運,終於走上人生巔峰! 天子
-
八十年前,尹修為了突破極限,追尋更高境界,踏上了前往遙遠的星空彼岸的路途。 八十年後,修為瓶頸,意識到心結未了的尹修又從星空彼岸的修真界回到了地球。 然而,八十年光陰逝去,地球上早已發生了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2014NextIdea原創文學大賞參賽作品】群號:199488169!期待您的加入!一個差等生,一次偶然的意外。讓他獲得了修真第一功法,從此命運徹底的改變。修煉異能,保護校花!用爆表的力量
-
他曾是國家最強利刃,一次大戰,身受重傷的他選擇退役,成為一名普通大學生,從此潛隱花都。 他身懷古武絕學,暴打權貴惡徒,你狂,他比你更狂!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古武狂兵》還不錯
-
新書【《女神的超凡高手》】已經發布,歡迎大家關注~! ======= 新書【《女神的超凡高手》】已經發布,歡迎大家關注~! ======= 新書【《女神
-
李謙重生了。 另外一個時空的1995年。 在這裡,他當然比普通人更容易獲得成功。 但成功是什麼? 錢麼?或者,名氣?地位?榮耀? 都是,但不全是。 有了那回眸的淺淺一笑,那牽手的剎
-
當撲面而來的時代巨瀾把懵懵懂懂的沙正陽捲入其中時,他是隨波逐流,風花雪月,還是長纓在手,逆流擊波?干想幹的事,為恣意人生。做該做的事,為家國情懷。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
一代兵王含恨離開部隊,銷聲匿跡幾年後,逆天強者強勢回歸都市,再度掀起血雨腥風!簡單粗暴是我的行事藝術,不服就干是我的生活態度!看頂級狂少如何縱橫都市,書寫屬於他的天王傳奇!依舊極爽極熱血!(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