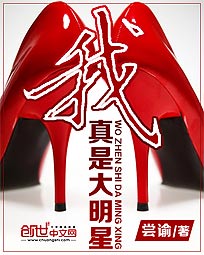半生煙雲 二十七 長臨工 下
readx; 師徒關係的改善緣於一場病。農工宿舍流行瀉肚子,頡顛尤其嚴重,拉膿拉血水米不進。葉小娜隨舅舅牛秋石來良種站出診。
三個月不見,小娜臉色紅潤長高不少,穿白大褂脖子上掛聽診器。牛大夫確診是急性菌痢,每人派發口服藥。蔣樂生說頡顛的病情嚴重,央求小娜給他靜脈滴注,老頭很快轉危為安。
深秋的一個雨天傍晚臨下班,頡顛突然問他看過三國沒有?樂生回答初二暑假裡看過。頡顛問可記得官渡大戰?他說當然記得,歷史上以少勝多的戰例嘛。頡顛又問:曹操手下有個叫王垕的會計,記得嗎?
蔣樂生狐疑不解:沒有呀,那年代哪有會計?
古時後錢糧官就是會計。頡顛以略帶傷感的口氣敘述:曹操久攻袁紹不下,面臨軍糧斷供危險,密命錢糧官王垕大斗改小斗,一天糧食勻做三天吃。王垕明知道剋扣糧餉是死罪,但主公命令不容違抗,只得遵命照辦。
蔣樂生說:這錢糧官後來好像被曹操殺了。
老頭點點頭,沉浸在自己的敘述里:大斗改小斗兵士怨聲載道。一旦發生譁變不攻自潰。曹操對王垕說吾借汝人頭一用,汝妻兒老小自有吾照應。手起刀落將其梟首,人頭掛旗杆頂示眾。後續軍糧運到,曹操重新發起攻勢,將士奮勇衝鋒大獲全勝。你說說,王垕死的冤也不冤?
渾濁的淚水在老頭眼圈裡打轉,蔣樂生吃驚地問:師傅你怎麼啦?
於是頡顛向他袒露自己的身世:哪年哪所大學畢的業,哪年哪月進船廠,做事用心被聘為總會計師,廠長令他做假帳偷稅——當時全國偷稅成風,要不怎有後來三反五反?廠長說你會計水平高,做的帳出不了事,出事我負責。不了出事後他推得一乾二淨!這白臉曹操讓我充當了一次王垕的角色!
頡顛泣不成聲,胡茬上閃著淚光。來北大荒前最後一次會見,老婆哭成了淚人,捧出離婚協議對他說,為了兒子你就簽了吧!
蔣樂生見他哭得傷心,安慰道:師傅別難過,一切都過去了。
頡顛的話象開閘的渠水:後來才知道,我離家不久老父也死了,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一宗不少!唉,我的歸宿,也就是棋盤山半島花園了。
老頭沉默片刻止住淚慨嘆:創辦立信會計學校的潘序倫,號稱中國近代會計之父,是我的大學同窗,責怪我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不懂得當會計危險係數高!
蔣樂生截住話問:師傅,危險係數高什麼意思?
老頭說,自古以來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可見錢財二字的份量。要守住錢袋絕非易事!你記住,說一千道一萬,犯法的事堅決不干!
頡顛借給他一本潘序倫主編的《會計學》,其中有兩章是自己的得意之作。
沒有業務實踐讀《會計學》味同嚼蠟。學問學問一學二問,在頡顛這裡行不通。向他請教只答一兩個字「對」「不對」「可以」,或者「自己動腦筋」。老頭說問人只學到皮毛,自己「悟」才明白精髓——也許他以此作為不肯施教的藉口?
頡顛對樂生的業務進步喜憂參半。元旦前會計檢查,任科長當他面誇他名師出高徒。老頭聽了雖高興,想到徒弟學成他將被棄之不用,心中不免悽惶。
應了潘序倫大師的話,會計這行危險係數確實高。
這年的春節物資依然匱缺,豬肉少得可憐:幹部基本工人及其家屬每人一斤,就業農工半斤,犯人只有三兩。
王化舉給生技科打報告,請求淘汰兩頭老牛,承諾上交場部機關部分牛肉。
「禿角」「老黑」的大限到了。劊子手便是會拉手風琴的王長脖。判刑前他是大連食品廠屠宰工。血腥的職業和風雅的業餘愛好集於一身,令人匪夷所思。
兩頭牛皆為雌性。「禿角」幼時淘氣,與夥伴角斗折了一隻角;「老黑」溫馴,名字由「大黑」而「老黑」。它們犁地拉車多年育有滿堂兒孫,如今毛色暗淡老態龍鍾,站著打瞌睡躺倒了懶得起。王長脖將它倆牽出牛圈,拴在相距不遠的兩棵樹上。它們不知死到臨頭,耷拉著眼皮呆呆佇立,任憑孩子們奔走呼叫一動不動。兩頭小牛犢撒歡兒跳前跳後,不知是誰的後裔?
王長脖摘下狗皮帽甩掉大衣,往手心呸呸吐兩口唾沫,拎起十二磅大錘,對準「禿角」腦門便是一錘。「禿角」像堵牆轟然倒下
二十七 長臨工 下
-
為美人無限張狂;為兄弟兩肋插刀;為親人誓死守護! 終極教官,當世大魔王重返都市。 面對強敵,他無所畏懼,鐵拳破之;面對美人……只可遠觀不可近瀆的未婚妻、嫵媚入骨的世家小姐、
-
看膩了刀光劍影,鼓角爭鳴,或者可以品嘗一下社會底層草根的艱苦營生。 本書講述的是穿越大明落魄寒門的沈溪,在這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年代,用他的努力一步步改變命運,終於走上人生巔峰! 天子
-
關於透視邪醫混花都: 窮學生陳軒,無意中獲得絕世邪醫傳承,習得醫道聖手,開啟透視神瞳,從此縱橫花都,恣意風流!各路極品美女紛紛而來,陳軒表示我全都要! ……
-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拒嫁豪門:少奶奶99次出逃》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推薦哦!
-
【2014NextIdea原創文學大賞參賽作品】群號:199488169!期待您的加入!一個差等生,一次偶然的意外。讓他獲得了修真第一功法,從此命運徹底的改變。修煉異能,保護校花!用爆表的力量
-
這是由一株人參引發的血案! 重生七八年,沒有空間,沒有錢,唯一挖到的一株野山參也被某個滿臉正氣的綠軍裝要求見面分一半。 林微脖子一梗,要錢沒有,要命一條! 誰知某人給了錢,要了命,管了她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世事如棋,有人身在局中當棋子,有人手握棋子做玩家。 大玩家擺弄蒼生,小玩家自得富貴。 秦風活過一世再重來,睜開眼,便要從棋子變玩家。 然則大玩家不好當,姑且,就做
-
人死的時候會有意識嗎?會,因為我經歷過。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鬼嗎? 有,因為,我就是。借體重生後,現他有一個美到窒息的老婆,睡,還是不睡?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最佳女婿》還不錯的話請
-
一心想當明星的張燁穿越到了一個類似地球的新世界。電視台。主持人招聘現場。一個聲音高聲朗誦:「在蒼茫的大海上,狂風卷集着烏雲。在烏雲和大海之間,海燕像黑色的閃電,在高傲地飛翔……暴風雨,暴風雨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