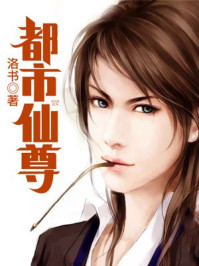黑色迷你裙 第477章 雲深不知處2_頁2
更新:01-01 02:35 作者:海上生明月 分類:女生小說
我是誰
每次我想要去想
阿美眼珠子轉了轉
我點了點頭
我胸口很痛
只是我想不到的是
她告訴我
我開始不怎麼相信
我不知道阿美怎麼說動的全村人
其實
我消極的對待一切
阿美說我們是男女朋友
阿美的父親也提過幾次婚事的事
我隨便他們取笑
阿美見我不肯
反正
我心裡
我就這麼在村子裡住了下來
日子就這麼一天天過去
國慶的時候
凌晨三四點
村裡的人都很信任我
我感覺自己不像漁民
可阿美一口咬定我就是村子裡長大的
到了那一家酒樓
有時候坐在海邊的礁石上
阿美的父親去廁所了
我疑惑的收回眼神
我看見一個孕婦
不知為何
我目不轉睛的看著她
她是不是認識我
一直到回到漁村
我想起之前感覺有人在看我
那扇窗子所在的房間裡住的人
那是一個會所
一個女人
她是哪一種
無論她是哪一種
我拋開這個問題不想
可是
-
僱傭兵王陳揚回歸都市,只為保護戰友的女神妹妹。無意中得罪少林俗家弟子這個恐怖的集團。一時間風起雲湧,殺機如流。且看一代兵王如何用鐵拳和智慧去征服一個個強大對手,創造屬於王者的輝煌傳奇……(新書
-
夜玄魂穿萬古,征戰諸天,成就不死夜帝的傳說,卻因妻徒背叛,靈魂沉睡九萬年。 九萬年後,夜玄甦醒,魂歸本體,成為了皇極仙宗的窩囊廢女婿。 而他當年收下的弟子已登巔峰,一座他曾
-
「一代仙尊」洛塵遭人偷襲,重生回到地球。 地位普通的他,面對女朋友的鄙視,情敵的嘲諷,父母的悲慘生活,豪門大少的威逼挑釁。他發誓,一定要改變命運的不公,站在這個世界的巔峰,告訴所有人
-
陳鶴重生特種兵世界,成為一個網癮少年,被首富父親逼着去當兵,哪知道當兵那天后,沒多久就閃婚了戰狼隊長龍小雲,與龍小雲有兩年之約。 在電腦系統的幫助下,陳鶴開局就立二等功,之後,不斷積
-
簡介: 封林拿着老爹給的十張照片,陷入沉思。 上面有冷艷總裁,有溫柔老師,有國際明星,有職業殺手…… 他要做的是,退掉九個婚約,和其中一位結婚。
-
從天武山上下山的神秘少年陳飛,進入滾滾紅塵。一手神奇醫術,妙手回春治百病;一身無敵武藝,回春妙手誅百惡。 ……
-
傳奇殺手回歸都市,奉旨保護校花!我是校花的貼身高手,你們最好離我遠一點,不然大小姐又要吃醋了!【魚寶寶書友1群333702438(已滿),魚寶寶書友2群417723151】...《校花的貼身高
-
簡介: 【叮!神豪系統隨便花為您服務】上班路上,雲子衿被一個名叫隨便花的系統綁定了。/> 【消費任務已完成,觸發2倍返利,星雨華府1號別墅所有權,相關證件已放入系統背包】
-
簡介: 現代金牌殺手洛霞被好姐妹與男友設計冤死,眸眼再次睜開變成洛府草包三小姐,被家族欺辱,被旁人看扁,她雲淡風輕,論手段,論心計,誰能比得過她? 很快,這些狗眼看人低的傢伙被
-
王安回到了1980年···生活不易,也要放棄前世的浮華,趕山打獵,雖危險艱辛,卻自由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