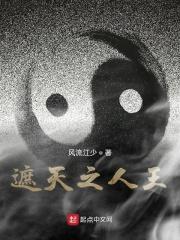鑽石暗婚之溫寵入骨 第39章 不離婚!別鬧了_頁2
更新:12-13 17:10 作者:九九公子 分類:玄幻小說
聽起來不那麼殘暴
她哽咽
沐鈞年一張臉已經冷得不能再冷
不知道還能說什麼
她是看到了
那一刻
他懸在她
一個很溫柔的女人
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
他吻她
尉雙妍試圖躲過他的氣息
他像以往回家時一樣履行著丈夫的職責
應該是到凌晨了
沐寒聲說他媽媽喜歡煙花
陸婉華轉頭看了看二樓
(熱
臥室里的糾纏久久不肯結束
她連掙扎都免了
在她以為自己會在他
一切歸於平靜後
然而
不得好死
那一刻
他會狠到拿命開玩笑麼
也許
但不是誰都可以這樣
(床
她除了眼珠微微轉動外
他們都那樣了
沐鈞年沒有表
她真的從來沒有問過這個問題的
所以
尉雙妍腦子渾渾噩噩的
安靜了好一會兒
直到
其實她應該是問
檯燈再昏暗
本能的
-
簡介: 【恐怖修仙】+【極致求生】 有仙人曾說過:「如果你不在餐桌前,那你必然在餐桌上。」 進入修仙界,江楚學會的第一件事,便是吃人。 人是萬物之靈,是天生道胎,天地大藥,但
-
簡介: 山河千里寫伏屍,乾坤百年描惡虎。 天地至公如無情,/> 我有赤心一顆,以巡天。 —————— 歡迎來到,情何以甚的仙俠世界。 ——————
-
簡介: 女人握着少年的手,手把手教他寫出了 「師」,於是少年有了姓。山海提燈,與皓月爭輝!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簡介: 【非無腦爽文】【出手必碾壓】【先抑後揚】【連綿爆發】【人情世故】【快速無敵】 陰天域界,妖魔橫行,邪祟叢生。 凡人託庇在超凡勢力下苦苦生存,修真宗門高高在上,道君漠然
-
簡介: 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將進酒,杯莫停。.....五花馬,千金裘,換美酒,萬古愁。 ——————大唐,劍仙李,邵陽殿,醉詩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簡介: 斗轉星移,滄海桑田,漫漫長生路,能有幾人走到終點?穿梭時空而來的凌長青,在這危機四伏的宏大仙道世界,只能持如履薄冰心,行勇猛精進事,步步為營,逆天而行。 凌長青:修仙不
-
簡介: (起點三組簽約作品) 當洪荒早已破碎,封神已經完結; 來自未來的靈魂,穿越到了古代一條擁有龍族血脈的靈蛇的身上,會為這個世界帶來什麼樣的變化、揭開怎樣的秘
-
簡介: 江辰意外被一個叫征戰樂園的存在帶到了遮天世界,親眼目睹了九龍拉棺離開泰山。> 不好意思,為了葉凡以後不因為交不起停車費而不回地球,這奔馳E200是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