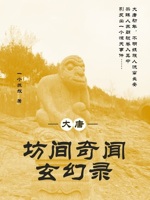英靈時代,十連保底 第四百五十六章 東方鴻,我日你仙人_頁2
更新:01-15 11:13 作者:蘋果咖啡味 分類:懸疑小說
沒有多少忌憚
因為眼前這位任南北
其對某些人的威脅
因為他完全是磨刀霍霍向世家和權貴
白榆甚至想到了這麼一句詩
任南北眼睛大亮
他甚至爆了粗口
任南北聽到這麼一句後
他拉著白榆袖子就不鬆口了
白榆急忙打斷
白榆哭笑不得
不過是一句
那我要是帶出來一句
那小眼神和小動作都出賣了他在扯淡的事實
或許是剛剛被白榆刷了一波好感度
任南北這話甚至不是對著慕遙夕說的
一名先天英靈血脈甚至不足以讓他提起重視
若不是今日白榆在這裡
因為他是驕陽
慕遙夕的意見並不重要
她自從接受白虎堂主後
這已經證明了慕遙夕並無掌握白虎堂的能力
放在過去
但現在不一樣
白榆聽出了言外之意
他皺眉道
任南北攤手
白榆不解
任南北面露無奈
-
李毅吧熱帖:兩年前被我甩的丑逼,現在是我們學校的校花!兩年前,她是丑逼,我是男神;兩年後,她是校花,我是屌絲。三天被打七次,我也屹立不倒!你看,我以前能保護你,現在也能保護你。左飛兩年後,左飛
-
愛藍天,愛綠樹,更愛波瀾浩瀚的大海。 淺海魚,深海魚,龍蝦還有大海蟹,吃貨的世界怎麼能少了海鮮? 快艇,遊艇,海釣艇,還有巡航艇,其實豪華遊輪才是王道。 家裡養着棕熊、白熊和浣熊,漁場還
-
四年前,徐東放棄大好前程,為愛挺身而出,嘗盡苦楚。四年後,重獲新生,卻不料未婚妻即將嫁給自己昔日的兄弟。徐東衝冠一怒,誓要問個對錯,沒想到陰差陽錯間,獲得天醫門老祖的傳承。從此,踏上醫道修真之
-
簡介: 防火防盜防閨蜜,老婆太聽閨蜜的話,說啥信啥。梁燦文原本和和睦睦的小家庭,因為老婆太聽閨蜜的話,最終離了婚。 離過婚的梁燦文綻放了戀愛第二春。直到有一天,前妻看到最信任的
-
簡介: (雙潔1v1,冷艷千金VS深情偽浪子)世人皆道霍藺浪蕩不羈,對女人走腎不走心,直到有一天這位高嶺之花紅了眼,折了腰,在雨夜裡卑微祈求, 「蔣璇,我求你別走……」&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簡介: 【美食+娃綜+萌崽+萬人迷+追妻火葬場】【女主開局即滿級廚神! 輕鬆爽文!】【清冷腹黑大美人x瘋批謫仙大佬x反派崽崽】南枝從美食世界滿級歸來,才發現自己的身體被異世靈魂
-
演員?演員的盡頭是帶貨!我可是大網紅,做演員?腦子進水了?
-
楊明是一名普通的學生,某一天,他收到一份禮物,一隻神奇的眼鏡,從此生活變得豐富多彩。 (魚寶寶書友1群 333702438)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很純很曖昧》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
-
簡介: 「青梅竹馬+單女主+葷素搭配+雙向暗戀+日常文+無系統無金手指+治癒救贖」 「老作者新書,坑品有保證! 」 晏殊有個小青梅, 從小到大跟他對着幹那種, 幼兒園他給班裡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