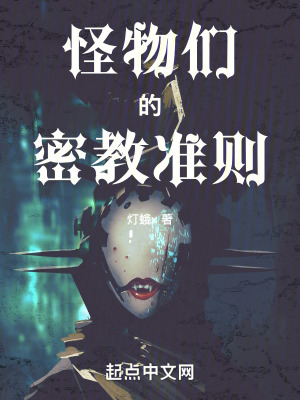朕真的不務正業 第四百八十四章 到底是誰帶壞了陛下?_頁2
更新:11-14 08:10 作者:吾誰與歸 分類:科幻小說
制度設計的內因
而王崇古給出的辦法是更多的物質
大明真的太大了
朝廷實行的變法
物理上消滅皇帝
這就是等級森嚴
常用的落水這種過時的手段
舊貴們更不願意掀起
大明皇帝遠在天邊
而且掀起民亂的惡果除了噁心一下皇帝
陛下手裡有牌
陛下手裡有兩張牌
朱翊鈞將手中一本彈劾王崇古的奏疏放下說道
馮保思索了下說道
馮保思索了片刻說道
馮保選擇了實話實說
他拿起了一本奏疏
萬曆十年三月
大明三年才三百名進士
這些年
現在海瑞在士大夫心目中
-
你說我一個鄉下進城的務工人員,怎麼就成道觀的觀主了? 青梅竹馬,醫生,警花,校花,環肥燕瘦,秀外慧中......這女律師竟然是拉拉?什麼,已經被掰直了,我什麼也沒做呀? 玄
-
簡介: 超紀元年,外星異族強襲地球,部分人類覺醒異能,世界逐漸瓜分為七個勢力所統治。/> 一邊是群雄爭霸,一邊是共同抗敵,還有遊走於天平兩端的人類極端組織。 某天,
-
簡介: 【軍婚+重生】寧媛重生回七十年代,她再不當隱忍抑鬱到死的好女人,虐極品、上大學、縱橫古董界,拼事業。 活成別人眼裡作風不好,永遠嫁不出去潑辣有錢——老姑娘但一天到晚懷疑
-
簡介: 陸瞳上山學醫七年,歸鄉後發現物是人非。 長姐為人所害,香消玉殞,br/> 兄長身陷囹圄,含冤九泉; 老父上京鳴冤,路遇水禍, 母親一夜瘋癲,焚於
-
簡介: 我的爺爺很古怪,他每天給自己上香,站在自己的靈位前吃蠟燭。村裡的人都很怕爺爺。r/> 我也很怕爺爺。後來我才發現,他們害怕的不是爺爺,而是我。爺爺也很怕我。
-
簡介: 一朝睜眼,人在大燕。 楊束對自己的身份很滿意,定國王府的獨苗苗,雖然皇帝猜疑,各家排斥,不過問題不大,他會造反。 做紈絝就要有紈絝的樣子,第一件事,劈砍老丈人……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簡介: 你是否想過,在霓虹璀璨的都市之下,潛藏着來自古老神話的怪物?你是否想過,在那高懸於世人頭頂的月亮之上,佇立着守望人間的神明? 你是否想過,在人潮洶湧的現代城市之中,存在
-
簡介: 一八四零年秋。世界如上浮之鯨,於少年眼中燃起烈火。一封十幾英里外的信,一個來自異鄉的旅人,幾段妙麗奇想的故事。 儀式者,奇物,異種,無形之術;咒殺秘文,尖耳朵貓貓龍,地
-
簡介: 【絕不聖母+快節奏+劇情緊湊+情緒不斷!】前世,江恆禪精竭慮當人人愛戴的大師兄,結果慘遭魔頭陷害,被正派人士圍攻致死! 重生後。什麼?魔頭?你是在說我嗎?想起前世的種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