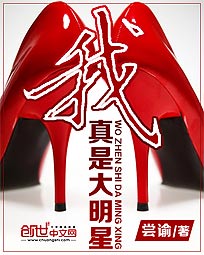帝王之友 8.夜用_頁2
更新:04-21 08:35 作者:馬桶上的小孩 分類:女生小說
士扮相
這男子便是之前混賬爹說的族中崔南邦了
好一個奇葩
&要你來了
&可莫要像你這樣
看起來比崔式年輕幾歲
他眉毛淡淡的
崔家這幫人怪不得傲上天去
崔季明算是聽說過
&你長子
崔式領著南邦去看了一眼妙儀和舒窈
舒窈也沒想到
妙儀不好意思的擦了擦鼻子
崔季明轉過臉去皺了皺眉頭
祖父崔翕在先帝時期不但是尚書右僕射
清河崔氏雖負盛名
這種門第
對於清流傲然崔家來說
南邦仔細的打量了一下崔妙儀
舒窈對於他摸了那禿毛老驢又來揉她頭髮一事有幾分不滿
&看起來就像是作詩詞之人
&記不太清了
舒窈轉了轉眼
南邦沒想到她這般大膽伶俐
&床遍展魚鱗簟
玉人共處雙鴛枕
他還沒念完
-
簡介: 神農之巔,蘇文下山結婚,不料卻被高冷未婚妻當眾撕毀婚書。礙於師父的囑託。 蘇文娶了高冷未婚妻的姐姐,陸晚風。陸晚風一直以為蘇文是山里來的窮小子,沒車沒房,直到有一天……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陸江仙熬夜猝死,殘魂卻附在了一面滿是裂痕的青灰色銅鏡上,飄落到了浩瀚無垠的修仙世界。 兇險難測的大黎山,眉尺河旁小小的村落,一個小家族拾到了這枚鏡子,於是傳仙道授仙法,開啟波瀾壯闊的
-
簡介: #日六,中午12點更新,感謝支持正版~ #專欄內預收《被表嫂逼嫁之後》求康康呀 大學生明遙期末考試結束,熬夜打遊戲猝死,穿成了古代安國公府一個庶女。 明遙:
-
簡介: 從【奔跑】,到無視物理的【神速】。從【瞄準】,到跨越因果的【必中】。 從【養生】,到久駐人世的【長生】。從【健身】,到血肉飛升的【化龍】。 重活一世的薛璟,在得到
-
暫時無小說簡介
-
一心想當明星的張燁穿越到了一個類似地球的新世界。電視台。主持人招聘現場。一個聲音高聲朗誦:「在蒼茫的大海上,狂風卷集着烏雲。在烏雲和大海之間,海燕像黑色的閃電,在高傲地飛翔……暴風雨,暴風雨就
-
簡介: 公元1572年,距離明朝滅亡、山河淪喪還有72年。此時東南倭寇橫行,西北韃靼叩關,地方兼併日重,軍政疲憊百姓困苦,隆慶皇帝剛剛駕崩。 石越卻在此時,穿越到了歷史上三十年
-
「從出生開始,我每天都會做一個同樣的夢,夢裡不斷重複着同樣的一天。」「你在夢裡都做了什麼?」「搶銀行、炸大樓、泡妹子、俠盜飛車……反正是夢裡,自然做了很多無法無天的事。」「說說你昨晚做了什麼吧
-
程岩原以為穿越到了歐洲中世紀,成為了一位光榮的王子。但這世界似乎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樣?女巫真實存在,而且還真具有魔力? 女巫種田文,將種田進行到底。 各位書友要是覺得《放開那個女巫》